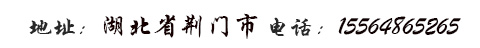人在潮汕,粥在砂锅
|
文/周建苗 很喜欢公司的早餐,是那一锅热气腾腾的粥。粥汤黏稠,米汤浓郁,看着凝脂的米浆,弥着袅袅白烟,散着淡淡清香,盛上一碗,配以花生、葱蛋、乌橄榄等,空腹吃之,就这样刺激着味蕾,稳心、暖胃、养生,有一种家的味道。更为爽心的,是那1元/份的价格,是天底下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好事儿。 粥,李时珍曰“粥字象米在釜中相属之形”,会意字,从米,从二弓。“米”指小米、米粒,“弓”意为“张开”、“扯大”。“米”与“二弓”联合起来,表示把米粒从左右两边同时扯大,《释名》说“煮米为糜,使糜烂也”。小米,也称粟,五谷(粟、麦、稻、黍、菽)之一,粥是粟煮成的,《康熙字典》中说粥也叫“糜”。 粥的文化,在我国已有几千年历史。悠久的粥的文化,便有了“断齑画粥、断齑块粥、划粥割齑”成语,说的是贫苦力学、食物粗简微薄意思;而后的“群雌粥粥、煮粥焚须、粥粥无能”等,也诞生了更多的意义。对于粥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周书“黄帝始烹谷为粥”。在四千年前,粥主要为食用,年前始作药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有西汉名医淳于意(仓公)用“火齐粥”治齐王病,汉代医圣张仲景《伤寒论》述“桂枝汤,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便是有力例证。 “治粥为生命之源,饮膳可代药之半”,自中古时期,粥的功能便“食用”、“药用”融合,就有如现代人们所说的“养生”。食粥,能清热解毒、解腥化腻、滋补身体,这与潮汕近海多吃海鲜,后食粥解腥化腻养生有关。似乎,最能使食粥发扬光大的,应该数潮汕人。勤劳的潮汕人每天劳作出汗多,又渴又累、食欲不振的时候喝一碗热腾腾的粥,既充饥,也能养胃气、生津液。所以,潮汕地区有关粥的俗语也多,如“糜尽咸菜了”、“食糜补腹”、“鞋算卖除,插米换番薯”、“白粥配咸菜”等等。 对于潮汕人是“独一味”的粥,每个人有着一种灵魂深处忆苦思甜的情愫。脑海的深处,总也磨灭不了是过去的食粥的辛酸无奈岁月,而今天留存更多的是对一种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养生方式。潮汕人独特的食粥方式,也形成了独特的潮汕粥文化。 曹雪芹的“举家食粥酒常赊”,写出了《红楼梦》的千古美谈,也与潮汕人食粥有相似之处。潮汕三面背山,一面向海,独特的地理,以及自古的天灾、人祸,导致了潮汕人生存的不易。历史上潮汕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潮汕人生活水平低,人口多食物少,煮粥相对节俭。所以食粥,便成了潮汕人赖以生存,勤俭节约的生存方式,海边煮粥时加一些海产品,鲜甜美味,富于营养。 相传,有个厨师看到隔夜米饭甚多,为节约,便把它们放在砂锅中加水熬成粥,随手加了些海鲜到粥里。粥成后,散发出奇香,喝起来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郁而不腻。 北宋时期,潮汕名士吴复古与苏东坡是忘年之交;苏东坡被贬惠州时,吴复古曾携当地出产的青蟹数只前往惠州看望苏东坡。苏东坡令厨子杀了一只老母鸡,熬而取汁汤,然后加米与蟹同煮一锅,其味鲜美无比。苏东坡即兴赋诗:清新有句须留待,风味如君不可忘,蟹粥粥从此名扬天下。 其实,潮州是宋代的广东瓷都,潮州北关古窑址、南关古窑址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唐时这里已有较大规模的陶瓷生产。潮汕砂锅粥,也与古时发达的陶瓷有关系,就地取材,用砂锅煮出来的粥,别有一番独特味道。而经过多年的演变,勤劳、吃苦、聪明的潮汕人,便把食粥的吃法,吃出了新花样,新的创新,且层出不穷,代代相传。 潮汕砂锅粥,是天底下的一道美味美食,也是潮菜的一大特色,以其独特的风味,打开粥的难登筵席,“粥不出户”之说。潮汕地区靠海,向来海产丰富,用来入粥,鲜甜可口,风味尤佳。潮汕粥也五花八门,有鳝鱼粥、鱼头粥、虾粥、蟹粥、牛肉粥、瘦肉粥、龙虾粥、鲍鱼粥等等,把肉、海鲜煮出成了水米交融的饭靡,这是人类最易吸收、营养保持最好的饮食方法。陆游曾赞美说“只将食粥致神仙”,其实走在潮汕大街上,也到处可以看见虾粥、蟹粥、番薯粥等小摊粥铺,混进大街小巷便会让人大饱口福,流连忘返。 潮汕砂锅粥的选料很讲究,米主要选煮出来稠且香、爽且滑的品种,如珍珠米等;主料多选用水产品,如鳝、膏蟹、龙虾、海胆、鲍鱼等;配料有萝卜干、干贝、香菇、嫩姜、冬菜,在煮粥的过程中适时加入。其烹调流程是先用旺火把米、干贝煮开锅,中间加水产品、酱油、油、姜等,快熟时再放点鱼露、麻油,而虾、黄鳝等在粥煮熟时才放进去烫一下。味道可据口味调配,想清淡的可放芹菜加冬菜,爱吃咸香的可放葱花加萝卜干,喜欢吃芫荽的可撒一些到粥中…… 潮汕砂锅粥,能最大可能的煮出鱼肉的鲜美,好像鱼儿刚从水中捞出来的,与水米无间交融,让每一粒米都吸满了“鲜气”。所以吃潮汕砂锅粥,里面的蟹肉肥美鲜甜,虾肉口感弹嫩,粥黏稠,包裹着每一只虾和蟹腿,都融化在粥里,想想就知道它有多鲜甜,没有过多的烹调,却好吃得几乎吞掉舌头。轻轻舀一勺送入口中,轻轻一抿就能感受到它的鲜滑,柔腻如一的温热美味,让整个人立刻变得亲切温暖,这味道,怕是吃过一次就会念想着一辈子了。 宋代苏东坡有书帖,曰“夜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说,海中之人多寿,而食番薯故也。潮汕用砂锅煮出来的潮汕白粥、番薯粥也很有名。潮汕白粥呈胶状,是那种纯粹淀粉的胶质,虽然米多水少,吃起来却不觉得浓稠,米粒入口即化;番薯粥要放凉了才好吃,有粥的清香又有番薯的甜味,一小碗熬到火候的番薯粥,加上几碟小菜,一小口一小口,一股清香,别有一番风味。 在潮汕地区,一碗清清爽爽的“白糜”,可配的“杂咸”(小菜)很多,最常见的是以菜脯(腌萝卜干)、咸菜(腌芥菜)、贡菜、橄榄菜等,有酱瓜、香菜心、姜丝麻叶、咸菜黄豆、贡腐等,还有咸鱼、鱼饭、生腌蟹、腌虾姑、钱螺醢(黄泥螺)、薄壳米等,多不胜数。一碗粥,面前摆着眼花瞭乱、林林总总的盘盘碟碟,吃着就有如“帝王”般的享受。难怪有的外地人笑称:潮汕人喝的这一碗“白糜”,犹如帝王般拥有“后宫佳丽三千”,有如吃着“满汉全席”的饕餮大餐…… 潮汕人以粥养生,甚至视粥为“补物”。在中医看来,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旺则“百病除”。粳米平补,特别是熬出来的那层黏稠的“粥油”,不但易消化,如果再加上新鲜美味的各种海鲜,营养更丰富。所以,对于长期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或是病后虚弱者,喝新鲜粳米熬的粥,确实滋补,所以潮汕也有“粥水养人”之说。 作为一个潮汕人,我常在早上或晚上,抽时间煮一碗“白糜”,配两样“杂咸”(小菜),或是一小碟新鲜的蔬菜,犒劳辘辘饥肠的自己,吃着不但胃舒服了,心情也舒畅了。这便是人们所说的“慰胃”、“稳心”,平淡而又朴素的养生之道。 经常的,与三五好友,来到街边巷口、走进偏僻小巷,砂锅粥店,在有呼呼的夜风中,围着一锅现点现做、新鲜出炉的海鲜砂锅粥,喝出一身微汗,身子暖了,胃也舒服了,一天的劳顿可以消去大半。而对于那些在外的潮汕人,如今已背井离乡,回想起昔日在老家常吃的砂锅粥,乡愁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漫上心头…… 中国人食粥的历史源远流长,粥与中国人的关系,正像粥本身一样,稠黏绵密,相濡以沫。潮汕砂锅粥,里面蕴含着我国厚重而又悠久的文化气息,无论处在什么年代,何种人群,袅袅粥香中所透露的宁馨和温情,粥中淡而绵长的滋味,都是最能抚慰人心的。 而在喧哗的城市角落里,走进一家不很喧闹的餐厅,带上心爱的人,来一锅经过时间慢熬的粥,聊聊家常,谈谈世事,人生就这样,足矣。 欢迎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yiweia.com/dywtx/10618.html
- 上一篇文章: 22个涨停,涨幅超6倍九安医疗如何成为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