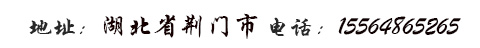苦笑夫子腩味
|
北京痤疮医院电话 http://baidianfeng.39.net/a_ht/210121/8612063.html腩味 作者▏苦笑夫子 1那天下午,生产队饲养场死了一头猪。 天已黑定,饲养员顾玉芳才发现死猪。顾玉芳在黑灯瞎火的饲养场里抹了几把泪,才偷偷摸摸来到队长全林家,跟全林说了这事。全林正在油灯下就着泡豇豆吃绿豆稀饭饭,听说死了猪,胃口顿失,把筷子“叭”一声摔在桌上,就同顾玉芳拉开一段距离,出门来到鸡市巷尽头的饲养场。 “这儿”,借着后窗微弱的天光,顾玉芳指指猪圈角落的一头死猪说,“也不知什么时候断的气,一发现我就来找你了”。语气中一半是哀怜,另一半是庆幸,因为还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气。说着摸出火柴,点亮挂在墙角的煤油灯。在发酵饲料散发出的浓重的酸腐气中,满屋密集的蚊子更加疯狂地盘旋着,轮番向两人进攻,同时发出“嗡嗡”的鸣叫,正如打翻了十二个蜂巢。 全林悄声惋惜道:“造孽!不是昨天刚请过兽医吗?花黑到底是什么病?”“花黑”是那头死猪的名字。饲养场总共三头猪,另两头分别叫花白和大黑。 顾玉芳撇嘴道:“请了还不如没请。把个猪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一针打下去,倒抽起风来了。他说是‘打火印’,所以没救。我看不像,可还是……”说着伸出一根手指,拭去眼角一滴泪,跨进猪圈去,把花黑的一条前腿提起来,“你看这腋窝的颜色,白白的哪有什么‘火印’?”眼神中就显出某种期待。“打火印”是一种恶毒而凶猛的猪瘟,年来在西坝一带流行。症状是高烧,同时在双腋下生出乌红的斑块,像烙铁烙过一般。得了这种瘟疫的生猪,大多活不过二十四小时。随着大批生猪的死亡,人们对它的恐惧,竟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 全林并不看猪。他知道顾玉芳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明知不能遂了她的意,又不忍心开口说出那瘟猪理当如何处置。却趁着顾玉芳跨出猪圈的机会,假装用右手去扶她,左手却在女人的屁股上狠狠捏了一把。顾玉芳的男人在青川大山里修保密工程,已经三年没回家了。 顾玉芳这回生了气,一巴掌打开全林的大手,朝全林瞪一眼,恨恨地说:“分了吃还是埋掉,放个屁!”旋即走到一边去。 全林嗫嚅半天才说:“埋。” “又不是‘打火印’,为什么不能分?”吃了“打火印”的瘟猪,十大队死了两个人,七大队死了一个,是最近的特大新闻。据说那死去的人,胁下的“火印”,同病猪毫无二致,还一样地发高烧,一样地抽筋。 “兽医都说了是,你敢保证就不是?不是‘打火印’也不能分。所有瘟猪都不准吃,县上早发了文件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全林无奈地说,“扑”一声吹灭煤油灯,朝顾玉芳走过去。 “滚!”顾玉芳失望地低喝一声。 全林扫兴,便转身朝屋外走,一边扭过头去吩咐道:“别声张!” 2母亲点着煤油灯,坐在楼门口纳鞋底,听见有人敲后门。母亲下楼开门,迎着杨妈。杨妈也不进屋,只把嘴巴凑到母亲的耳朵旁。 “花黑到底死了!”杨妈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死了?” “死了。千真万确。” “埋还是分?” “傻瓜。分我就不找你了。埋。兽医说是‘打火印’,顾玉芳说不是。也不知谁对谁错。” 母亲喜出望外,口里却说:“你怎么知道这些?” 杨妈便说她去鸡市巷找会计算工分,从饲养场后窗下经过时,看见里面有灯光。她踮起脚跟,凑近窗口,本想悄悄看一下生病的花黑,却恰好听见里面两个人的动静。说到后面,两人都忍不住暧昧地笑。 笑毕,就郑重其事地商量起来。 杨妈和母亲是闺蜜。打伙弄吃的,是她们共同的喜好。她们蒸出的粉蒸肉,又大又肥又咸,儿女们一块也吃不完。她们做出的醪糟,香甜无比,我吃了生出满脑子的幸福感,同时也因为过敏,长出一头肉唧唧的大包。不过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回,她们又将打伙求吃。 杨妈走后,母亲上楼灭了灯,就坐在窗口看街上。全林住在我家的左斜对面,母亲料定全林掩埋花黑,就在今夜不久之后。彼时,她将偷跟了去,看他埋在哪里。 3全林回家,就着青蒿熏蚊子的满屋烟味,“稀里呼噜”喝完刚才的剩饭,用屁股在屋中间那盘大磨的磨盘上挤出一块地方,坐下,长长吁出一口气。 十年前,全林家开着面粉坊,专为国营的粮站磨面粉。如今,粮站的面粉早改用机器打磨,拉磨的老牛也早死了,全林家这盘大磨就闲置起来,上面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积满了灰尘。 全林刚坐下,又站起来,去屋角拿一把锄头,习惯地在地上一筑,提起来,好像要出门。犹豫一刹,却并不就走,只拄着锄把,重新坐下。全林太知道一头半大的花黑,在生产队一百三十多口人的心目中,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花黑活着,是今年过年的希望。花白和大黑还很小,注定过年出不了栏。如今花黑一死,远期的希望没了,眼前的希望却突然降临。如果全林一声令下,把花黑弄干净了,按人头分下去,就在今夜,家家户户都将笑逐颜开,男女老少都将油光满面。明天,一队所有人见了他的面,都将投来感激甚至谄媚的目光。从过年到如今,人们就没沾过一星半点的油腥。让他们吃回肉,是无量的功德,也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事。 可是全林不敢冒这个险,那责任太重大了。不说“打火印”,任何瘟猪都可能致人死命,先例层出不穷。真弄出个什么凶险,他担待不起。然而要将花黑埋掉,又实在可惜。半大的花黑,长得圆滚滚的,毛重怕有六十来斤吧。虽是瘟猪,却是囫囵一整头。如果不生这场病,养到过年去,肥了,到国营屠宰场杀掉,国家征去半边,剩下的不到五十斤,还不如现在的花黑。他要征购,你不敢不“自愿”出售,否则就是“私杀生猪”,而“私杀生猪”是重罪,他曾害得润生获刑三年,现在想起来都胆寒。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经地义。瓜豆尚且如此,经年累月养出一头猪来,却生生地被人抢去一半,全林于心不甘。虽是给了钱的,可钱却买不来油水。一队老少的肠胃早锈迹斑斑,油水比钱更值钱。养猪的一年到头吃不上半斤肉,不养的却每月一斤,吃得红头花色,脑满肠肥。全林每念及此,就恨得咬牙切齿,造反的心都有了。花黑之死,是上天怜悯送来的福分。今夜分了花黑,那功利比花黑没死还要强些,更少费半年工。真要埋了去肥地,才是伤天害理。再说了,那七大队和十大队,吃瘟猪的人肯定不止三个。既然只死了三个,就不是死于猪瘟,也太有可能。这么一想,全林的心又活泛开来,就将那把锄头放回墙角去。 就这样翻来覆去,全林在磨盘上折腾到半夜。最后,还是长长叹口气,换了件黑衣,提起锄头,疲沓出门而去。 全林来到饲养场,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摸到那个角落,抓住花黑早已僵硬的的后腿,一扬臂,就把花黑披在背上。出门上锁,出巷口向东,一溜烟上了六面山。那夜有月,月却在云背后。幸而是晴云,白而薄,就有朦胧的月光,罩着幽暗的山野。全林强健,贼一般在红苕地里窜跳,循相反的方向,绕六面山跑了大半圈,来到场南头江西会馆后山的坟场。确信背后并无跟踪人,这才一耸身,轻轻放下花黑。全林把锄头往地上一搭,坐下擦把汗,休息片刻,然后挖坑埋了花黑。 全林本想把剩下的新土撒得远远的,让人看不出痕迹,思量再三,却没有实行。遂提了锄,从南路下山,到白马河对岸转一圈,做出给稻田放水的样子,这才回家。此刻正是夜阑人静之时,那一钩残月正在白云间忙碌地穿行。 4母亲虽出生于旧时,却是天脚,所以跟踪全林,并不费力。母亲见全林绕着六面山的山腰转圈,知道他是想甩掉身后假想的跟踪者,让花黑入土为安,不受侵犯。母亲一边暗笑,一边停止追踪,直接爬到山顶。六面山的植被,本是遮天蔽日的,如今却只剩稀稀拉拉的几株小桐树。所以母亲在山顶以逸待劳,反把全林的行踪,尽收眼底。见全林在坟场停下,母亲差点笑出声来。 母亲不会用成语。如果母亲会用成语,她会说全林用心良苦,却多此一举——其实,从饲养场到江西会馆后面的坟场,只需喝一碗稀饭的时间,可是全林饶了一大圈,却足够煮出一锅稀饭。 江西会馆后山的坟场,有五六十座古坟。墓碑林立,密密匝匝。其间稀稀落落地穿插着几十株老桑树和老榆树。此处荒僻阴森,人迹罕至,多半不因了它的坟茔,而是因了多年以前,它是一个杀人场,先后有十三名西坝各乡押来的犯人在此枪决。说不定哪株老树嶙峋的皱皮中,就嵌着某犯的脑浆或穿透的弹头。所以在最饥荒的年月,也没人敢去剥那里的榆树皮,吃那里的黑桑椹。类似的杀人场,西坝还有两处。母亲想,不过就埋个花黑,全林你犯得着选这种地方么。 然而毛头小子全林都不怕,母亲岂会怕。所以母亲在山顶之下、坟场之上的一块台地边,居高临下看着全林把坑挖得差不多了,这才不无遗憾地下山找杨妈去。母亲遗憾的是出来时没带背篼,要不片刻之后,就可以把死猪背到杨妈家去,独占其功。母亲不敢也没有力气像全林那样,把死猪直接扛在身上走。好在去杨妈家并不远,也就吃一碗烫稀饭的路程。 5母亲和杨妈顺场后的田坎路到鸡市巷口,在一块菜地边南行几十步,左拐抄近路上山,很快便进入坟场。 “第一排——左手第三块墓碑——正对出去——第一棵桑树下——”母亲在心里确定着方位。果然看见了零乱的新土和明显的土包。两人的心遂狂跳着,麻利地挽起袖子,提提裤脚,蹲下,运足全身之力,用手扒起来。 我的伟大的母亲们,人人都有一双钢铁般坚强、棉绒般柔软、美玉般温润、天工般灵巧的手。亘古以来,就是这些瘦骨嶙峋、青筋暴突、皮开肉绽、指甲缝中嵌满了污泥、因为长年累月的劳作而不能伸直、骨节突出、甲尖锋利如鹰爪一般的手,收种皇天赐与的本应足够的五谷,缝补后土赐与的本应足够的衣物,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子孙。当要从豺狼虎豹的口中夺回儿女的生命或食物的时候,母亲的手和她们的脸一样狰狞。当为远行归来的游子抚平创伤的时候,她们的手则因深情似海而柔若无骨。为让儿女的前程一路平安,她们的手就如锋利的斧钺,直接地披荆斩棘。当苦难潮涌般连番袭来的时候,她们的手又如擎天之柱,为儿女们撑起一片苟活的空间。母亲的手,是造物的首创,是生命的火炬,是爱之花,恨之剑,是人类的光荣与骄傲。 我曾经无数次地观察母亲的手。那手小巧玲珑,不愧是造物的杰作;却又坚韧强劲,鹰隼也叹为观止。当它们灵巧地翻动起来的时候,那十个指头的绝妙的配合,曾让我眼花缭乱。然而凑近了看,那手掌上竟布满厚实的老茧,掌纹似黑色的沟壑,手背上累累重叠的新创伤和旧疤痕,记录着百战不殆的殊勋。裂纹和伤痕之间,嵌进大小的刺棘,随手就可以拈下好几根。还有很多细刺,不易直接拔出,母亲就拿缝衣的针尖,写意地挑出。每每挑出一根,就冒出一滴殷红的血珠。因为过度紧张的劳作,几乎每年夏天,母亲的手都要得一回腱鞘炎。正所谓“十指连心”,母亲的腱鞘炎一旦猛烈地发作,便照例坐在父亲的圈椅里,拿好手捧住病手,悲惨地呻吟,然后就泪如泉涌。那不是为自己的痛苦,而是为儿女们暂时失去的呵护。 那时的我们,果真就像一群无助的雏鸟,躲在一边,凄凉地同母亲一起垂泪。于是不出三天,母亲的手就好起来——医院为何物,那是伟大母爱的药力将其治愈的——新一轮无休止的劳作便又开始。 然而这回,两个母亲将那地方刨了一个很深的坑,直到刨出生土了,都不见花黑的影子。她们便很沮丧,恨自己太过小心,出来晚了,让人占了先机。遂胡乱盖了土坑,背起背篼,一步三回头地往回走。走出几步,目力欠佳却耳朵特聪的母亲似乎听见坟茔丛中有人“嗤”地笑了一声。母亲在心中算计,时间如此之短,那先到的贼子不可能已经下山,遂拉着杨妈走远了,再从树影下蹑足潜回来,躲进一块墓碑后去。母亲和杨妈相视一笑,虽看不清彼此,却明知是会心的笑:不远处那座最大的坟墓旁边,果然浮起一个人来,一个熟悉不过的女人。 6顾玉芳接手饲养场五年,算上花黑,共死了三头猪。前两头都不如花黑肥大,分别埋在狮子山背后的坡地和杨氏祠背后的坟地,都是当夜就不翼而飞。公社离得近,不意间听到风声,还派专人把全林叫去,骂了个狗血淋头。 全林很丧气,但不是因为挨骂,而是责怪自己屡屡糊涂,为防范本队人而把瘟猪埋在边界附近,结果一头被二大队的人偷去了,一头被本大队四队的人偷去了。早晚被人偷,真不如让本队人占了便宜。全林后悔,给顾玉芳发过誓,将来埋猪,一定找个隐秘的地方。 今夜全林又要埋猪,顾玉芳便寻思:本队的隐秘荒僻之地,除了前两处,就剩下江西会馆背后的坟地了,而且此地不与外队搭界,即令花黑被盗,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其余地盘,都是西坝场周围袒露无遗的小块平川,稍有动静,便引来众目所视,并不是花黑的葬身之地。所以全林第一次离开饲养场,顾玉芳就透过自家的门缝,密切地窥视着鸡市巷。 顾玉芳家坐落在平桥头一条名叫尿巷子的小巷的旁边,背靠白马河,隔着街道可以将鸡市巷看个对穿。全林把花黑背出饲养场往东走,顾玉芳并不跟踪,只壮着胆子出西坝场南头,向右兜一圈,绕过江西会馆上六面山坟场,藏在坟地背后的树影下远远地坐等。虽有点不自信,却到底不出所料。只恨该死的全林把时间压得太晚,竟害她担惊受怕地等了大半夜。 全林虽是个优柔寡断的细心人,埋葬花黑的活,却干得很粗率。全林一走,顾玉芳三五下就刨出花黑的一只脚,捉住一拖,花黑就出了土。顾玉芳用脚把坑边的松土拢回,做恢复原样,才去管花黑。花黑虽已僵硬,却并未腐败。顾玉芳将它拖到宽阔处,套进带来的麻袋里,扎了口,提起来抬腿一托,当胸抱起,踉跄着正要往肩头上搭,却听北头小路上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响过来。虽不知如何走漏了消息,却肯定这两人是冲着花黑而来,遂慌忙放下麻袋,就近拖入一个巨大的墓窟中。这墓的墓碑早倒了,只好在墓旁树影下的草丛中将就藏下。那座坟是同治年间的,因为树碑人姓廖,住在江西会馆对门的廖文才,便一口咬定,那古墓的主人,是他先祖的先祖的先祖。 顾玉芳见那两个落魄人忙活了半天,最终两手空空,悻悻而去,把嘴一撇,忍不住得意地笑了一声。估计两人走远了,慢吞吞把自己移到墓窟边去,拖出麻袋,提起来用膝头一顶,抱在当胸,正要往肩上搭,忽觉眼前一黑,天旋地转,那麻袋就“噗”一声滑到地上。顾玉芳明知那是自己身体本就虚弱,又在野地里蹲得太久所致,心里倒也不慌,准备缓口气再来;那钩弯弯的残月,却叛徒一般从云缝中探出头来,不偏不倚,正巧把光束打在她身上。 顾玉芳的男人姓黄,是母亲的本家。母亲把顾玉芳当成自己的小妹,一向怜爱有加。此刻,母亲见顾玉芳如此狼狈,知道时机已到,遂“噗”一声先把杨妈的背篼扔出去,再拉了杨妈一同站起。那顾玉芳正在运气,看见墓碑后滚出一样黑乎乎的东西,早吓得半死;继而又见墓碑后冒出高矮两条黑影,更是魂飞天外,一头乱发竟倏地呈放射状蓬松起来,头却不晕了。两条黑影便“吃吃”笑成一团。 顾玉芳说:“吓死我了!我正愁一个人……” “愁死活该!这就是吃独食的报应!”杨妈揶揄道,心里却想:你一个人吃不完,还不兴用盐巴腌起来?见母亲已经走过去,把麻袋拖起来,拿背篼装了,背上,三人欢天喜地从南坡下山。这条路杳无人户,比走鸡市巷隐秘得多。 7三人的预谋,是从南场口廖文才家旁边的小路过去,下河沿,顺白马河岸边走,到平桥桥头,从吊脚楼的后门到顾玉芳家。顾玉芳是主家,又是饲养员,有她在,就该在她家收拾花黑。可是过了马路上小路,就在廖文才家后门旁,埋头走在前边的杨妈,却与挡道而立的廖文才撞个满怀。 杨妈骂声“砍脑壳的,吓人一跳!”几人便站下。 廖文才五十来岁,生得尖嘴猴腮,正是三十年代在渣滓洞当过伙夫因而一辈子脱不了干系的那位。 “早料到今夜有人送礼,却不曾想从后门来。也不先打个招呼!”老廖调侃道。 母亲是个出名机敏、嘴快的人,知道泄了密,便说:“晓得有客人送礼来,也不先作个准备?” “嫂子别急,老廖我早准备好了!”廖文才返身往回走两步,拉开后门,果然有贼亮的灯光,拥着一团热气流出——廖家把烫猪的开水都烧好了。 廖文才的婆娘拿围裙擦着手,笑吟吟地把一行人让进屋。就见廖家大小参差的八个儿女,正兴奋地站在屋角傻笑。廖文才的亲哥一家四口,也早从隔壁过来。还有廖文才的亲哥的准亲家,生产队的会计,也在一旁公事公办地坐着。十七八人,就把一个逼仄的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大家七手八脚将瘟猪取出,却见花黑的肚子已经鼓胀起来,且从眼鼻等处,流出股股浊臭黑红的粘液。顾玉芳见此光景,又可怜起花黑来,就躲到一边去哭。两个男人和四个女人开始忙活,弄了半天,总算把花黑变成两片肉和一堆下水,摊在桌上,却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便有被惊醒的苍蝇,分成几个集团,一轮又一轮,顽强地猛扑过来。众人正在会计领导下热烈讨论分配方案,谁去管苍蝇?只廖文才的大儿黑娃凑过去,埋头闻闻,赶紧捂住鼻子,把眉毛拧成一个黑疙瘩,一边摇头一边嚷道“呸呸!好臭!”躲得远远的。 廖文才见状,也去闻闻,却大不以为然,将嘴一撇,骂黑娃道:“你晓得个狗屁!这叫腩味!老子当年在渣滓洞,有个当官的就单好这一口,别人想吃还不给呢。只是那时机不好掌握。时间短了没有腩香,时间长了又臭得不能吃。我的经验,这时的花黑,就恰到好处!也多亏它在我廖家祖先的阴宅中走了一遭,多少沾了点仙气……” 话未说完,顾玉芳跳起来喝道:“你个老不死的敢跟踪我?”抓个扫帚扑过来就要打。 廖文才一边躲一边说:“只准你瞄全林,就不准我瞄你?我又没起歹心!”顾玉芳就红了脸更要打,闹了好一阵才完。 8生产队一共二十八家,除去半农半商的六家和有政府干部的四家,一共十八家。就估摸着按人头把花黑分成大大小小十八份,连下水也分尽了,由在场人分头送出去,只猪头给廖文才家留着。全林那份最小,因为他只有两口子。由母亲送去,交给他婆娘吴菊珍。大家相信,全林饶是个不讲情面的队长,也抵挡不住腩味猪肉的诱惑,所以断不会闹将起来,告到公社去。 都在那个大喜大庆的凌晨,几乎在同一时间,西坝公社一大队六生产队的十八户人家的房顶上,都冒起淡蓝色的炊烟。 母亲亲自烧一锅开水,撒把盐进去,再放进猪肉,很快煮熟了。捞起来,给父亲留出一小部分最肥最端正的,把剩下的切成片,就叫起一家老小,全吃下肚里去,再把啃过的骨头丢回锅里。母亲许诺,明天中午,将用这些骨头和肉汤熬出一锅油稀饭来,届时将多加两把米。 END闲谭编辑坚持乡土情怀支持闲谭原创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yiweia.com/dywpz/8584.html
- 上一篇文章: 蚝油不是酱油,记住ldquo三不放三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