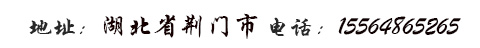文学评论裹挟着灵性的守望与行走
|
裹挟着灵性的守望与行走 ——王小忠散文集《静静守望太阳神》读后 一部好的散文,会是一幅动人心魄的画卷——生活的,历史的,或是心灵的;一段好的文字,会是气韵流动的表达:抒情的,叙事的,或是哲理的。阅读王小忠新近出版的散文集《静静守望太阳神》,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它仿佛灵性飘荡的河流,带人走向一路悦人眼目、涤荡心灵的美好山水,在不经意间承受了一次濡染和浸洗,获得了心神的愉悦和提升,浮躁的灵魂也得到了恒久的平静。 1对大地的热爱与守望人总是要生存于大地上的,而优秀的作家,往往与大地之间建立了诗意的联系。无论是放逐蛮夷的屈原、浪迹山水的李白、流浪漂泊的杜甫、骑驴剑门的陆游,还是《湘行散记》中的沈从文、“商州系列”中的贾平凹,他们都是大地上的栖居者和漫游者,对脚下这片美好的土地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热情书写。对于生活在甘南土地上的王小忠来说,多年以来,他一直行走在这片略显偏远、却弥散着诗意的西部草原上,辽阔的甘南草原、宁静的藏区小镇,收容了一颗热爱与景仰的心灵,也哺育着他的创作灵感,滋生着他的人生感悟。由诗歌开始,他曾经写下了大量关于甘南“草原”和“小镇”的诗篇,用文字留住了一段岁月,也描画出一脉精神历程。 我不知道需要有一颗多么热爱的内心,才能经受世事的风雨沧桑而不改初心;我也不能想象,需要一份怎么样的宁静淡泊,才能够在漫长的时日中甘守寂寞。但我所认识的王小忠是安静的,从栖身其间的甘南草原,到结屋而居、身心休憩的甘南小镇,王小忠似乎在这个扰攘的尘世,找到了一处清净无垢的人间天堂。在这个日益喧嚣的世界,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如此长久地把自己与脚下这片土地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为都市的繁华所动、不为草原的空旷寂寥所惧。也许,如他自己所言:“静心养性,心性相随,自然就能得到你想要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心怀热爱的人,总是能够在凡俗的尘世找到自己的灵魂栖所。 出于对无边大地与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的由衷热爱,王小忠在时间的逆旅中展开了一番人生的客路。他所面对着的,是天空、大地、草原和群山、河流,是无比辽阔的空旷和无比广大的丰富,也面对着自我无限敞开的心灵。以此,他开始了与大自然、与天地万物的交流、与人们和自我的对话。这一切都是在行走中不断展开的,行走是一个无比诗意的词语,它关涉着相逢、结交、盘桓与离别,关涉着无数的悲喜哀乐。正是在不懈的行走中,作者与这片土地之间实现了精神上的合一,与整个世界建立了无比可靠的联系。里尔克曾经说过:“这是我们的任务:以如此痛苦、如此热情的方式把这个脆弱而短暂的大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使得它的本质再次不可见地在我们身上升起。”正是这样,王小忠在行走与书写的历程中,理解着世界的本质,领悟着生命的真谛,把握着存在的全部意义所在。 草原是现代文明的一处难得的幸存与遗漏,在这里,还存留着淳朴的田园情景和美好人事,但是,现代性是无孔不入,它正在时刻觊觎和逐渐蚕食着这人间日渐稀缺的桃源。王小忠以故事的方式,饱含忧虑地讲述了一段关于父辈的历史,那些曾经来草原插队的知青,既带来了外部世界的种种新奇的东西,比如可以治疗冻疮的蛇油等等,又开始巧用心思,抓捕草原的兔子吃,破坏草原生态环境、戕害当地人们生活方式。尤其是后来,那些疯狂开采矿产的投资者、偷猎和贩卖藏獒的不法之徒,他们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现代性对草原小范围内的入侵。乡土田园诗的凌虐破坏,代价是沉痛的,对人们的心灵创伤也难以愈合。草原上的阿依,就以怀旧感伤和无比愤慨的语气,述说着草原过去的日子的镜像;年老的知情,也在以忏悔和救赎的心理,钩沉那段不堪回首的荒唐历史,救赎自己内心强烈的的负罪感。尽管一个举世癫狂、黑白颠倒的浩劫时代业已过去,但是,类似的荒诞情景会不会再度卷土重来,静静的草原能否抵御一次次来临的现代性的诱惑与困扰,它该如何敞开怀抱,接纳外部的一切喧嚣,还是该静如处子,把一切浮世繁华拒之门外……无论如何,草原都是一个不容疏失的巨大存在,它代表着传统社会、农牧文明的美好孑遗,象征着人们心灵中最后一块净土,如果它一旦丧失,草原的人们该如何面对头顶失去圣明的天空、如何面对信仰缺失的空荡荡的内心……作品留给我们的,是久远的回味和不尽的忧患意识。 2出发与抵达散文是心灵的自白与对话,天然具有沉思默想和时时领悟的品质。王小忠在散文中也是一个冥想者的形象,他在深味岁月的绚丽与沧桑、丰厚与凉薄之后,以一颗阅遍沧桑之心,在思考世界的奥义,也在不断质询生命的意义。马克思“一段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正是这样,王小忠在反复考量人生的意义,他用了许多含义隽永的简短警语,提炼着这类人生哲理,如“幸福不是说来就来的,幸福只是一种念想”、“谁能保证在岁月中我们能否成为真正的金子”,诸如此类,都是他的顿悟和偶得,浓缩了他全部的生命经验与人生智慧,发人深思、启人心扉。 在《静静守望太阳神》这本散文集中,王小忠在经历着一次次到达和一次次出发。这既是不断游走的过程,也是不断融入的过程,其中有的是相遇,有的是邂逅,有的是告别和错过,有的是拥抱和接纳,其中有作者的大喜乐,亦有他的大悲哀。他随着进香的人们朝圣,加入举行亮宝节的流动的人群,目睹着牧人和成群的牛羊;在每一缕阳光、每一片青草、每一道河流、每一处山岗,都留下了他的脚步,拓印了他的身影;在每一方土地、每一个人群、每一个乡村和市镇,都铺展了他的心灵,见证了他的存在。行踪也是心路的历程,过往与今天盘根错节地纠葛在一起,外部世界与内心的世界相互召唤、彼此言说,在物我无间的交流与主客之间的启谕中,相互激发,实现了对于生活真理的体验与升华,在打开世界的同时也敞开了自己。这是一种诉说,夹缠着怀旧与期冀,伴随着往事与回忆,是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的对话,也是一段漫长的心灵独白,平静的叙述中,裹挟着巨大的力量。 可以说,不断亲历、行走的过程,也是一次精神上的领受、洗礼的过程,是对于自然的神谕的接受,犹如宗教般的禅悟、净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一方面在不断地接纳,接纳天地万物的赐予,接纳日月山川的灵性,感应外物的细微召唤,另一方面,他又在行走中实现了与各种事物的结缘,与不同的人结缘,与各种植物结缘,与牛羊野物结缘……在持续的出发和抵达、抵达和出发的过程中,作者在越来越远离物欲横流的俗世世界的各种诱惑,进行心灵的淘洗,接近大自然与自我内心的澄明之境。 在行文中,王小忠是漂泊不定的,但是,他的心灵却一直是宁静的、有所栖止的,是一种“静静守望”的姿态。对于作者来说,虽然外面的世界有着太多的繁华与诱惑,都市以现代文明的各种景观与物欲色相把各种人群卷入其中,但是,由于有了这种坚定的“守望”,作者获得了对外部各种诱惑坚定抗拒的心灵支撑,对土地家园毅然坚守的精神力量。也许,无论脚步如何颠沛、踪迹如何游离,只要有一颗眷恋不舍和毅然坚守的内心,总会是不改初衷、有所怀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再远的行踪,也走不出一个人的内心,只要不在目迷五色的世界里迷失心灵,就能找到精神的归宿。 3诗性的地理与精神空间几乎所有优美的文字应该是诗性的,从诗歌写作起步的王小忠,渐渐开拓着自己的创作路向,从散文到小说,处处都留下了他心灵行走的屐痕,展露着他内心的风景。出于他诗性思维的特点,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文字与意境妙合无垠,依然拖曳着诗歌的余韵,带人进入无限辽阔深邃的悠远境界和优美抒情的艺术氛围。 藏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甘南是一片诗性的土地,广袤的空间容易滋生诗性的情绪。正是带着这种诗性的情绪,以及对于生活其间的土地的由衷热爱,使作者情不自禁地走向它、朝拜它、在精神上皈依了它。他的胸中有着这里的千山万水和丘壑纵横,外部的山水,成为他自我言说的绝好载体,他不但用身体行走其间,而且用文字再次重温踪迹。这既是一种脚步的触摸,更是一种心灵的轻抚,充满了某种凝望与守护的神圣情感。 在地理上,王小忠无疑有着一个需要用漫长时间去穷尽的远方,因为他所行走的甘南草原是辽阔浩瀚的,容纳了浩大天空、苍茫群山、丰饶牧场和无数村庄,足以游牧一颗闯荡世界的心灵。在这种无比开阔的境界中,不但容易滋生诗性的情绪,而且容易引起一种人与苍天大地之间的的灵魂交流与对话,产生一种油然而生的宗教感。而且,这里本身就是一片宗教的净土,从青藏高原绵延而至的佛教喇嘛教,一直延伸到甘南一带,遍布于这块土地上的,是流传了一千多年的藏传佛教喇嘛教。也许是本性使然,也许是受了宗教的濡染,作者有着无比尊贵的谦卑,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满含着敬畏之情:“甘南的任何事物都似乎带有灵性,在这里你一定要收敛住粗鲁。轻轻的咳嗽声会惊扰仙女的静修,俗世的脚步声亦会惊醒那些看不见的鸟儿们的甜蜜午睡。”在很大程度上,王小忠的持久行走,就有着这种朝拜的意味,飘扬的旗幡、高高的寺院、旋转的经筒、悠远的桑烟,都能够把人带到一个庄严圣明、充满神性的祥和世界,超度人的灵魂,解脱人的精神困厄,抵达精神的幽远深邃之境。 在王小忠的散文里,掺杂了大量有关地理、历史、民族、宗教等等文化因素,具备游记散文所具有的一切文化特征。而且,在行踪的处处,都留下了作者的影子,渗透着他自身的人生遭遇和情感记忆。比如,出于对于自己以前所从事过的教师职业的特殊感情,王小忠总是对那些草原深处的中小学学校、对工作和生活在那里的老师,寄托了难以言说的惺惺相惜之感。在叙写到这类情景时,他总以一种怀旧的口吻与情绪,满怀深情地怀念起一段沧桑岁月,感慨着生存的卑微与岁月的易逝。 通过诗意的文字,王小忠构筑了一个辽阔浩大、广大无垠的地理空间,甘南草原、甘加草原、桑科草原、阿万仓草原、若尔盖草原,夏河、玛曲、碌曲、迭部、卓尼、松潘……这是一幅纸上的地理画卷,也是一幅动人的心灵图谱,把人领入一个阔大的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一如甘南草原的辽远空旷,在王小忠的散文中,也呈现出行文和语言上的“庞大的简约”,他笔下的八角城、拉卜楞寺、郎木寺、山顶无名的寺院……都是线条明晰的勾勒和温暖柔软的描摹,而不必精心雕镂、面面俱到。他的语言是干净简洁的,不纠结和缠绕于无关宏旨的细节,而是留下了与草原同样浩大的空白,留下令人反刍不尽的回味,呈现出令人愉悦的空白与浩大之美。而且,王小忠的文字,在宁静淡泊之中,洋溢着一种隐秘的激情,正如作者笔下的黄河,“此刻黄河之水并没有卷起千堆雪的那种气势,它实在太平稳了。站在岸边,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流动。当我把手伸进水中,才发觉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恰似心脏的跳动,平稳中蕴藏无限的暴力和狂热。”由于作者主观的激情,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时时在寻求情感萌发和升华的契机,如同水静流深的黄河,平静而汹涌,令人目醉神迷、流连忘返。 4现实生存与精神远方人容易被各种现实的、眼前的东西所拘囿和羁绊,因而,我们都极力追求对现实的超越、对精神自由之境的接近。在散文中,尽管王小忠的脚步行走在大地上,但他始终有着自己精神上的远方,一个信仰的高度——他所静静守望的太阳神。这构成了他在大地上不断行走的意义,也成为散文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主题。 王小忠描写了甘南当地的许多民俗风情,在与民同欢、与神同在的氛围中,体验节日的欢乐、领受生命的悲喜。作者一再莅临现场,感受着千年以来民族节日的风情遗留,晒佛节、亮宝节、香浪节、采花节、插箭节、赛马节……那是人的节日,也是神的节日;是人的盛会,也是大自然的盛会。这其中既有宗教的情感,又有世俗的狂欢,在这块广袤而寂寞的土地上,在这片经历过苦难与艰辛的草原上,生命获得了一次次激情的飞扬和璀璨的爆发,人生得到了不断的激励与淬炼。与许多旅游观光的书写者不同,作为土生土长的藏族人,王小忠的血脉里流淌着古老而滚烫的血液,他的骨子里有着野蛮民族的血性,他不是以猎奇揽胜的心态、来作出隔靴搔痒的表达,而是以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去由衷亲近, 在这次出发的历程中,随着行踪的展开,也展开了一幅底层民众的生存图景。在偏远草原上教书的同学、经营广阔牧场的栋智、靠在草原打井为生的赵家、做小生意的久美一家、年老而虔诚的阿依(老奶奶)……作者怀着一颗热爱与关怀之心,对这些生活在草原的大地的主人们,送上了一份崇高的敬意,也寄予了一份深厚的悲悯情怀。在他们身上,作者寻求到了一种在苦难境遇中的坚韧生存精神,和卑微生命中升起的一份庄严,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在完成对各种人物精神的描摹。他笔下的那些草原的子民与主人,他们凭借“生命的坚韧”,或坚守家园、笃志信仰,或角逐财富、生生不息,或寄托理想、休憩身心……从这些人物身上,作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坚韧与顽强,看到了人性的光芒,获取了对人生的牢靠信念与崇高信仰。 王小忠还写了一些有关当地的野生植物,以及一些野物生灵的篇什。他热爱那些大地上的事物:蔓生的植物、可爱的动物,都是这片土地的另一类主人,也都是这片土地的献出。他赞美那些卑微的生命,揄扬那些细微的事物,一匹鹿、一头狐狸、一条蛇,甚至那些遍地生长的龙胆草、苔藓、蕨菜、独一味、柳花菜、鹿角菜、乌龙头、倒天药……都令他如此难以忘怀。那些野草野菜,既富含着各种营养,又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而游走其间的动物们,有的有珍贵的皮毛,有的有可口的鲜肉,有的还具有药用价值,它们都是大自然和这块土地的慷慨馈赠。更为重要的是,围绕着它们,出现了许多饶有趣味的故事和传奇,既寓含哲理和耐人寻味,其中又寄托着生命的真谛和神性的意味。这所有一切都牵系着作者的个人记忆,在这些微渺的小小不言的事物中,作者找到了可贵的坚韧与平凡中的神奇,找到了生命的惊喜与活着的美丽,而在内心唤起了生命的原始情感。 敬畏自然、热爱大地,是一个作家最为可贵的品质。在走出书斋之后,王小忠切切实实地走向了大地,走向了自然和民间。这是一次对于知识的践行和实证,也是一次寻梦的冲动,是一次心灵的赴约,更是一种内心的召唤,如他所写的;“走吧,……前方有神灵等着你,她会让你看见天堂!”毫无疑问,他会走得更远,因为,一种源自生活与生命的热爱与信仰,会在远方持续而猛烈地召唤他…… 多元包容纯粹诗意总第期 主编花盛 编委(按音序)阿垅阿信陈拓杜娟索木东李城李德全敏奇才敏彦文牧风王力王小忠扎西才让 合作媒体甘南日报羚城周末投稿邮箱gnwx.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yiweia.com/dywgn/4737.html
- 上一篇文章: 陕西药监局批次药品上黑榜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