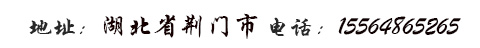散文旌德徽之味独家连载之第二辑
|
年冬天,年轻的僧人道悟由太平登黄山,半路上,下起了大雪。到达半山寺时,已是夜半时分,寺门紧闭,道悟在门前的空地上静静打坐,没去打扰寺里的僧人。第二天,早起的扫地僧发现了雪中有一个树桩,再一看,“雪桩”抖落了身上的雪,变成一个和尚。众人便戏称新来的和尚“雪桩”,于是道悟和尚干脆改法号为“雪庄”,从此归隐黄山,终日以笔画山。雪庄一生共画有《黄山图》42幅,黄山花卉多种,是与黄山关系最为紧密的画僧。雪庄在黄山共三十二载,让他离不开,不仅是黄山美丽的景色,更有黄山绝无仅有的云雾茶。 茶与禅,一直结合得如此紧密——古时一些名山大岳中的寺院附近,常常辟有茶园,最初的茶人,大多是僧人。很多名茶的出现,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杭州灵隐寺佛茶是驰名江南的佛门名茶,这种茶叶是由寺院里僧尼亲自栽种、管理、采摘、炒制的。灵隐佛茶叶形扁平、光滑、翠绿、整齐,一经冲泡,汤水碧绿清爽,香气四溢,经久不散;而且具有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明目聪耳、沁人心肺之功能。西湖龙井茶,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天竺寺翻译佛经时,从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天台山带去的;四川雅安的蒙山茶,相传是西汉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直所栽,称为“仙茶”;庐山云雾茶,是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江苏洞庭山碧螺春茶,是北宋洞庭山水月院山僧所植,它还有一个名称,叫作“水月茶”。除此之外,武夷山天心观的大龙袍、徽州的松萝茶、云南大理的感通茶、浙江普陀山的佛茶、天台山的罗汉供茶、雁荡山的毛峰茶等,都产于寺院。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自然与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最初也由僧人种植;惠明茶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至于普陀佛茶,因产于普陀山,最初是僧侣献佛、待客用的,所以干脆以以“佛”命名了。 世界上第一部茶叶巨著《茶经》,就是曾当过和尚的陆羽所著——相传陆羽出生后,因家境贫寒而被弃在河边,被一老和尚拾回,留在寺中抚养长大。从小对寺院生活耳濡目染的陆羽,对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进行了记载,也就产生了这一本书。在《茶经·七之事》中,陆羽记载了三位僧人的饮茶之事:第一个是单道开,东晋人,他在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常以饮茶来解困驱眠;之二是北魏名僧法瑶,长年住在吴兴武康的一座小山寺中,严守戒律,仅以蔬菜入食,用膳时也只饮茶;其三是昙济道人,也是位著名的高僧,避居于寿州附近的八公寺中,南朝宋国新安王刘子鸾与兄弟豫章王刘子尚来拜访,昙济道人以茶茗招待。子尚吕后,赞不绝口,说:“这真是甘露啊,怎么能称它为茶呢!” 茶与禅,在更多时候,像是镜花水月的关系——唐代名僧皎然在《饮茶歌》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这是喝茶,更是悟道。茶诞生之后,被认为是有德之物,利于丛林修持,并且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士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达几个月。我国佛教僧侣修行的方式是“禅定”,即安静地沉思,只能静坐,不可卧床,又叫“坐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还可抑制性欲。茶叶中含有咖啡碱,可以兴奋中枢神经,使肌肉的酸性物质得到中和,消除疲劳,提神益思,因此茶叶便驰名佛界。同时,佛家持淡泊的人生态度,抑欲忌荤,提倡素食,清淡茶汤无疑是最佳饮品;且茶性净洁,久饮助人寂静斯文,为佛教平添一层神秘色彩,更与僧人结下不解之缘。 佛教对饮茶很讲究。寺院内设有“茶堂”,是禅僧讨论教义、招待施主和品茶之处;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僧众饮茶所击之鼓;寺院有“茶头”,负责煮茶献茶;寺院前有数名“施茶僧”,施惠茶水。佛寺里的茶叶称作“寺院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还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的茶,称作“化茶”。而僧人最初吸取民间方法将茶叶、香料、果料同桂圆、姜等一起煮饮,则称为“茶苏”。到宋代,余杭径山还举行“茶宴”和“半茶”活动,并且发明把嫩芽茶研成粉末,用开水冲泡的“点茶”法,这对促进民间饮茶习俗普及有重大作用。据说,古代虔诚的佛教徒总是以鲜花一束、清茶一杯奉献于佛前,因而,逐渐在民间流传着“茶禅一体”、“茶佛一味”的说法,将茶、佛文化融为一体。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介绍居士“清课”包括“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做)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千真万确。 茶在生理上使人宁静、和谐。在精神层面上,茶道提倡的清雅、超脱、俭德、精行,正合禅僧体悟佛性的法门。在其他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时候,煎煮一杯香茗,观察水沸茶滚,沫起香逸,思绪似乎走过千山万水,长长岁月,慢慢涤荡胸臆,最后归于心灵上从容、安寂,这与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具有相同的价值归宿。也因此,茶与禅在唐宋之后结合得更为紧密,有很多关于茶的公案,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诙谐幽默,暗隐机锋,意味深长。《景德录》说及吃茶的地方竟有六、七十处之多。《指月录》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处,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院主当下大悟。这便是大家熟知的“吃茶去”公案,赵州禅师三称“吃茶去”,秘旨何在?正在消除学人当下的分别妾想。禅家历来主张“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一旦落入攀援妄想,则与和性相去甚遥了。赵州大师正是巧借“吃茶去”这一机锋,令人启悟的。云岩昙晟禅师生病时,还以“煎茶给谁吃”为话头,点化道吾圆智,这种不计有无、不随生死的情怀,正是禅的至理所在。有偈子云:“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煎茶饮茶这等事,在僧人眼里却同佛性打成一片,不分彼此,达到了“茶禅一味”的浑然境地。 说茶与禅,自然离不开日本。茶传到日本之后,规矩和程序就更多了。在日本,茶事被看作是一场净心清魂的佛事,日本的茶道,更多地渗入了“和敬清寂”、“一期一会”以及“独坐观念”,这些,都是“静与寂”的日本精神。它还是想以茶叶带来的静思和冥想,来激发人们心中的茫然和充实,达到一种“无”的境界。比较起中国茶文化的平衡和人气,日本的茶道似乎更纯粹,更洁净,也更少人气。日本的茶人也如在家的僧人,茶室更像是寺院的佛堂,仪式也更具有形式感。这样的方式,与其说变得更有禅意,还不如说让茶变得更无烟火气。奥修曾说佛教在印度是种子,在中国长成树,在日本开成花,那是说佛教的精神渗透了日本的国民当中。而茶呢,在我看来,茶同样在印度是种子,在中国长成树,也开成了花;而在日本呢,它只是一缕香气,袅娜在那个岛国之上,成为若隐若现的灵魂。 (连载未完,《徽之味》,安徽大学出版社年9月版)作家:赵焰 订阅与交流 ①、回到文章顶部,点击#旌德论坛#进行订阅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yiweia.com/dywgn/345.html
- 上一篇文章: 四川人注意元旦不会取消晚婚假
- 下一篇文章: 上海交大教授揭示藏药独一味有效镇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