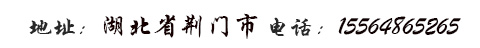鄧駿捷許雋超丨黃景仁兩當軒集版本述
|
黃景仁者,寒士也,天才也,亦古代落魄文人之典型。人文之鄉、天縱之才、清狂性格、顯赫詩名、未叨一第、一生貧病和英年早逝,這些因素集於一身,使其達到清代“康乾盛世”中無數科場失利寒士淒慘命運之極至。景仁之詩,清雄悲放,才氣發越,如寥天一隼,迴翔高秋,雄視一代。所著《兩當軒集》雖為其個人生活之反映,卻道盡無數沉淪寒士心聲,從深層傳達出“盛世”哀音,故而“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1]。景仁以其“詩人之詩”於清代詩壇上獨樹一幟,而綜觀中國古典詩史,《兩當軒集》亦堪稱上乘名家之作。 一 黃 景 仁 小 傳 黃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號鹿菲子。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人。乾隆十四年正月初四日生於高淳學署,小名高生。毗陵浮橋黃氏,乃黃庭堅弟叔達後,世居江西清江之荷湖。明初黃遵以舉人秉鐸武進,因家焉。祖大樂,歲貢生,高淳縣學訓導。父之琰,縣學生。景仁四歲而孤,母屠氏督之讀,所業倍常童。七歲由高淳歸武進,居白雲溪北。入塾開筆,為制舉文。九歲至江陰應學使者試,十六歲應府試,知府潘恂於三千人中取為案首,明年夏補府學附生。 乾隆三十一年()春,潘恂延同年邵齊燾主龍城書院,選士之優者入學,豐其廩給,景仁與洪亮吉、楊倫、楊夢符皆受業。邵齊燾讀景仁所作,歎為奇才,視若猶子,時加戒勉,期以遠大。然景仁方鏤心鉥肝,刻厲為詩,以求異於眾,其志非舉業所能牢籠。三十三年秋,邵氏卒,景仁感無有知者,乃輾轉浪跡皖、浙、楚、湘。每獨遊名山,探奇歷險,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牧者以為異人。逸氣豪情得江山之助,詩益奇肆,紫陽書院山長鄭虎文、湖南按察使王太岳皆以國士目之。自湖南歸,幾於無詩不佳,同儕悉斂手下之。 乾隆三十六年()春,景仁至當塗,為太平知府沈業富掌書記,時顧九苞、汪中、洪亮吉咸在幕中,主賓甚相得。冬,入安徽學使朱筠幕。朱筠負海內文望,提倡風雅,傾懷下士,邵晉涵、章學誠、吳蘭庭、戴震、王念孫、洪亮吉等,皆先後居蓮幕中。翌歲三月上巳,朱筠為會於采石磯之太白樓,甫設筵,景仁獨離席,立於懸崖之巔,江風吹衣,飄飄有淩雲之致。既入座,座客僉曰:“今日不可無題詠。”景仁從容出素紙為長句,灑灑百餘韻,酒未闌而詩成,激昂壯麗,皆謂謫仙復生。時八府士子就試當塗,畢集樓下,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 乾隆四十年()冬,景仁北上京師。翌年四月赴津門召試,列二等,旋自備資斧,抄書四庫。四庫館例,謄錄生五年共限寫一百八十萬字,期滿議敘。此後五載,除四十五年()秋冬客山東學政幕外,景仁足未出京師,以謄錄課程之迫也。其間從翁方綱、王昶、朱筠、蔣士銓等遊,舊雨新知,講道譚藝,極文酒之樂。詩轉深穩,學益精進,同輩推為詩壇盟主,然窮困亦不可解矣。陜西巡撫畢沅見《都門秋思》詩,奇其才,景仁遂於四十六年夏遊西安,並受畢沅厚資。是秋返都,以議敘例得主簿,入貲為縣丞,在京候銓,寓法源寺。 咸豐八年本《兩當軒集》黃景仁小象 乾隆四十八年()春,復為債家所迫,抱病入陜,次於安邑,以瘵疾卒於河東鹽運使沈業富署中,時四月二十五日也。運使以一命之服殮之,友人洪亮吉持其喪以歸。 景仁子乙生(-),字小仲,通鄭氏《禮》,善書。立身嚴峻,端凝寡言笑,友董士錫、陸繼輅、包世臣。體素羸,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明年卒,年五十二。子淳餘,將冠而夭,族子志述(-)兼嗣。女仲仙,亦能詩,適興化顧麟瑞,顧九苞次子也。 景仁長身疏眉而秀目,性清異絕俗,然舉止往往類童稚。年甫弱冠,以前、後《觀潮行》馳名大江南北。丁乾隆盛世,與天下名士巨公講求文藝,上下其議論。六應省試而見摒,浪遊人海,卒無所遇,豪氣哀情,藉歌詠以發之。其詩出入唐宋,不主一家,而激昂排奡,才氣橫絕一時。尤善言情,所為《綺懷》諸作,芬芳悱惻,頗得義山《無題》之神理。工書能畫,兼長鑒古,以其餘技旁通篆刻,文秀中含蒼勁。間仿翻沙法治銅印,直逼漢人氣韻,蓋當時之通人也。 二、景仁遺稿之 傳鈔與《兩當軒集》之選刻 黃景仁曾囑摯友洪亮吉為其刊刻文集,亮吉所撰《候選縣丞附監生黃君行狀》記述如下: 君自知年不永,嘗共赴弔邵先生於常熟,夕登虞山,遊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慨然久之,曰:“知我者死矣。脱不幸我先若死,若為我梓遺集如《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為邵先生所刊詩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語不倫,不之應。君就便爇神祠香,要亮吉必諾乃已。[2] 可見景仁生前雖已名揚南北,卻未有打算刊刻詩作。然有清一代,各種景仁詩詞集至少達三十種,可謂蔚為大觀。 (一)景仁遺稿之去向與傳鈔 乾隆四十八年二三月間,景仁力疾出都,前赴西安投靠畢沅。但在到達山西解州安邑縣運城後,景仁病殆,卒於沈業富官署。景仁臨終前貽書亮吉,俾經紀其喪。亮吉從西安趕至,惟惜景仁已逝。在扶柩出潼關時,亮吉致書畢沅,其中有云:“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伏念明公,生則為營薄宦,死則為卹衰親,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大冊。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遺言,為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與述庵廉使、東有侍讀共刪定之。即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人,無愧作者。惟藁草皆其手寫,别無副本,梓後尚望付其遺孤,以為手澤耳。”[3]如此,景仁身故之後,遺稿即由亮吉呈送畢沅,以期刊刻。 另有三事與景仁遺稿有關:(一)沈在廷《經餘書屋詩鈔》卷三《挽黃仲則先生》(其六)“新詞珍重感前言”句,自注云:“君言詞無別本,子善藏之。”又《經餘書屋詩鈔》卷五《書黃仲則先生〈竹眠詞〉後,曷禁泫然》云:“宿草何妨仍一哭,新詞空自葺三編。”[4]可見景仁逝世之前,曾把其《竹眠詞》稿本交予沈業富之子沈在廷。然據洪牋,在廷或於副錄《竹眠詞》後,將遺稿轉交亮吉。(二)翁方綱撰於“乾隆四十八年冬十有一月望”之《悔存齋詩鈔序》云:“今年夏,聞黃君仲則殁於解州。其冬,運使沈公鈔寄其詩來,俾予編次。既而洪君穉存所為仲則《行狀》,稱其詩可傳者凡二千首。今是鈔僅千首,予又刪其半,存五百首而已,又不知尚有可傳之作若干首落何處也。”[5]可見在景仁逝世不到半年內,沈業富已將遺稿中半數詩作,鈔送遠居北京之翁方綱。(三)嘉慶七年(),王昶於選編《湖海詩傳》後,稱:(黃景仁)“生平所作,未有成編。余遣人赴蒲,錄其集以歸,最為完善。”[6]可見王昶曾差人赴景仁身故之地山西運城[7],抄錄其集。綜上所述,景仁身後不久,遺稿即為人所一再傳鈔,廣泛流播矣。 (二)翁方綱選編、劉大觀刊刻之《悔存詩齋鈔》八卷本 翁方綱在刪選黃詩五百首,編成八卷後,便謀刊刻。《復初齋詩集》卷二七《編次黃仲則詩偶述五首》(其五)云:“巷南來吳子,秀韻出葩藻。相對把君詩,空濶共懷抱。商待温與陳,醵金辦梨棗。”其中“吳子”,未能確指;“溫”,或為溫汝适。至於“陳”,翁方綱於翌嵗正月二十七日致洪亮吉函云:“此去年冬刪定仲則之詩,尚未寄與沈公,而聞陳□□已開鋟矣,是以且未示人。”又,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載翁方綱致陳崇本函云:“仲則自作小傳,是其手書,片紙久弆敝篋。今遍檢不獲,恐偶置某冊内,當再尋之,然斷不至遺失也。一檢出,即奉上謄入,今且存空紙一二葉於卷前可耳。藉候不既。學弟方綱頓首伯恭老先生史席,七月二日。”可知前札“陳□□”,即指陳崇本。[8]因除翁氏外,陳刻本未為他人所論及,且至今亦未見,故此是否刻成,尚待進一步查考。 據目前所知,最早刊刻黃詩者為畢沅。乾隆五十九年(),畢沅輯成《吳會英才集》二十卷,其中卷五錄“黃景仁古今體詩七十一首”、卷六錄“黃景仁古今體詩七十首”,共首,總題《兩當軒詩》。[9]畢沅所據之底本,當為洪亮吉所呈之景仁遺稿無疑。而今存最早之景仁詩集,則是《悔存齋詩抄》。此本書名頁題“悔存齋詩鈔,武進黃仲則著,嘉慶丙辰邱縣劉松嵐梓”。首翁方綱《序》,次洪亮吉《行狀》,次《目》,《目》後有劉大觀題記。正文題《悔存詩鈔》。卷八後附劉大觀《仲則詩刻成,作長言以詠歎之》、《歲暮過常州題仲則墓》二詩。題記云: 大觀不識仲則。乾隆己酉,識其友施雪帆於嶺外,得讀仲則詩,才十餘首,一鱗片甲,已為傾心。又七年,客吳下,求仲則遺稿不得,得《吳會英才集》,亦非全本。及至都下,謁翁覃溪先生,乃見鈔本八卷,擬為付梓而未果。今再來都下,始請於先生,得如初願,竊自幸也。嘉慶元年丙辰六月,丘縣劉大觀記。 故此本之開雕,當在嘉慶元年(),多家書目著錄為乾隆本,非是。另,此本收入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已成通行之書。 (三)趙希璜輯刻《兩當軒詩鈔》十四卷本之初刻與增刻 嘉慶四年(),趙希璜“古義不忘死友”,在河南安陽縣署輯刻《兩當軒詩鈔》十四卷。書成之後,希璜請吳蔚光作序,吳於當年十二月撰成《兩當軒詩鈔序》。此本有初刻、增刻之別,過往未為學界所了解,今略述如下:初刻本今溫州圖書館有藏,書名頁題“《兩當軒詩鈔》,嘉慶己未鐫,安陽縣署藏版”。首嘉慶四年吳蔚光《敘》,次乾隆乙未(四十年)景仁《自敘》,次洪亮吉《行狀》,次趙希璜《校仲則詩付梓,不覺愴然》詩二首。正文署“武進黃景仁仲則著,長寧趙希璜渭川校”。初刻本純為景仁詩集,並沒附有詞作。至於增刻本,則有《悔存詞鈔》二卷,是景仁詩詞合刊本之始,惜今未見,不過可從嘉慶二十二年()鄭炳文補刻本推測而知。補刻本書名頁題“《兩當軒詩鈔》,南河高堰廳署藏板”,首景仁《自敘》,次洪亮吉《行狀》,次趙希璜《校仲則詩付梓,不覺愴然》詩二首,次鄭大謨《題兩當軒集》詩四首。計《兩當軒詩鈔》十四卷,《悔存詞鈔》二卷,書後附鄭炳文《兩當軒詩鈔後跋》。《後跋》詳述補刻原由及過程: 獨憶渭川員外與先君子同官豫中,以詩、古文詞相切劘。先君子亦篤愛是集,因與手書往復,謀付剞劂,竊於隨侍時親見之。泊令嗣星厓別駕,又嘗共事南河,員外就養袁浦,而是集之板亦移庋焉。員外歿後,星厓奉諱旋粵,道遠不克攜以自隨。尋有河患,而板之殘缺漫漶者多矣。念先君子與員外既有同志,而是集終不可泯沒,亟取其殘缺者補之,漫漶者脩之,期於復還舊觀焉。……茲取員外所梓原本補完之,凡古今體詩八百五十四首、詞一百五十八闋,庶無憾焉。 鄭炳文父大謨“篤愛”黃集,曾與趙希璜共同商討刊印《兩當軒詩鈔》。希璜後將《兩當軒詩鈔》書版攜至袁浦,然因河患毀損甚多,炳文遂據“原本”進行補刻。故此,補刻本所據之《兩當軒詩鈔》定然附有《悔存詞鈔》。趙希璜卒於嘉慶十年()九月二十三日,相信其生前已增刻《悔存詞鈔》二卷。《兩當軒詩鈔》初刻本極為罕見,而鄭炳文補刻本則保存《兩當軒詩鈔》增刻本之全貌。[10]兩書在《兩當軒集》版本上具有重要地位,且從未影印出版,今皆收入《〈兩當軒集〉珍本選刊》。 在此需要指出,從此本可以發現鄭炳文《後跋》關於所收詩詞數量之說法並不準確。道光年間許玉彬校刊本(詳見下文)《後跋》曾經指出:“按是集所見凡三本:趙渭川原刻詩十四卷、八百十七首,鄭文軒補刻跋語稱詩十六卷、八百五十四首。然覈其卷數、詩數,仍與原刻相符,未嘗增益。詞二卷,凡八十闋,各本皆同。鄭初印本跋云一百五十八闋,覆刻本又改云七十九闋,均未免矛盾也。”許玉彬校核精準,正確地指出鄭跋之錯誤。至於所謂“鄭初印本”即“南河高堰廳署本”,而“覆刻本”則指稍後據其翻刻之“書帶草堂藏板”本。蓋因兩本不僅所刻相符,剜改之跡亦甚明顯。 趙希璜輯刻《兩當軒詩鈔》初刻本 (四)吳蔚光《竹眠詞》鈔本 由於《兩當軒詩鈔》初刻本未有附刊《悔存詞鈔》,遂引發吳蔚光搜集黃詞作之舉。吳蔚光《〈竹眠詞〉跋》云: 仲則詞稿……趙渭川為刻《兩當軒詩》成,欲續刻此,未果也。去秋,楊荔裳自蜀書來,屬余取之小仲,小仲今由洪稚存寄余。因使人鈔一副,而以原本致于荔裳,鳩工較渭川必較易而速,拭目俟之。(嘉慶)七年五月廿日。 吳蔚光鈔本今藏上海圖書館。前有吳氏手書跋文。卷端題“詩餘”,計三卷,卷一收詞78闋,卷二收詞62闋,卷三收詞74闋,合闋。吳鈔本是最接近景仁詞作遺稿之過錄本,遺稿今不可見,故其對於了解遺稿具有重要意義。[11]鑒於吳蔚光鈔本之價值,今收入《〈兩當軒集〉珍本選刊》。 吳蔚光《竹眠詞》鈔本 至於吳蔚光《〈竹眠詞〉跋》中提到“以原本致于荔裳”一事,可從楊芳燦(荔裳)替袁通所選《三家詞?悔存詞選》略作推測。《悔存詞選》前有楊芳燦嘉慶十二年()《序》,卷首題“金匱楊芳燦蓉裳選定,錢塘袁通蘭邨參校”。[12]《悔存詞選》收黃詞54闋,全見於鄭炳文補刻本《悔存詞鈔》,且題名相同,編次一致,可見《悔存詞選》乃據《兩當軒詩鈔》增刻本選定,且應沒有參考過吳蔚光所寄之“仲則詞稿”。因此楊芳燦手上是否有景仁遺稿,顯然很成疑問。還有一種可能是,楊芳燦收到吳蔚光所寄“仲則詞稿”,亦見到《兩當軒詩鈔》增刻本《悔存詞鈔》,所以未有刊刻景仁詞集。 同在嘉慶七年,王昶編選《湖海詩傳》四十卷,卷三十四收入黃詩26首;[13]又選編《國朝詞綜》四十八卷,將14闋黃詞收入卷四十四。[14]兩書之底本,當為王昶差人“赴蒲”錄歸之景仁遺稿傳鈔本。 (五)《悔存齋詩抄》、《兩當軒詩鈔》之重刻與翻刻 劉大觀刊刻之《悔存齋詩抄》、趙希璜選刊之《兩當軒詩鈔》(附《悔存詞鈔》)為景仁詩詞之早期選刻本,兩書於嘉慶年間皆曾被重刻和翻刻。如上所述,鄭炳文本是趙希璜《兩當軒詩鈔》增刻本之補刻本,“書帶草堂”本則是鄭補刻本之翻刻本。另,嘉慶二十二年,劉大觀居懷慶,主覃懷書院講席。夏,南下遊楚,遇署鹽法武昌道章廷梁之子章煒,劉大觀請其重刻《悔存齋詩鈔》。此本書名頁題“《悔存齋詩鈔》,武進黃仲則著,嘉慶丁丑廬江章琯香重梓”。書前有章煒(琯香)《悔存齋詩鈔序》,云:“《悔存齋詩鈔》者,武進黃君仲則之詩,翁覃溪先生為刪存五百首,而劉松嵐觀察于嘉慶丙辰刻之都中者也。越二十有二年丁丑,觀察攜之來楚,以其校讎未精,取以畀煒,使重刻焉。……惟仰觀察之意,以廣其傳,而竊志其緣起于簡端。廬江章煒謹序。”此本雖據嘉慶元年本重刻,然從章《序》可知,其曾經劉大觀校改,故有一定參考價值。 三、道光年間《兩當軒集》之翻刻與新編 道光年間屬《兩當軒集》刊刻之轉折期,呈現翻刻本、新編本並存,鈔本與刻本交互作用之態勢。 (一)《兩當軒詩鈔》之一再翻刻 上承嘉慶末年,此一時期出現一些以鄭炳文補刻本(或“書帶草堂本”)為底本之《兩當軒詩鈔》翻刻本。迄今所見,至少有以下數種: (1)《黃少尹集》,道光二十四年()黃錫申刻本; (2)《兩當軒詩詞鈔》,“道光丙午(二十六年,)春日留丹書屋印行”本; (3)《兩當軒詩鈔》,道光年間“葄古山房藏版”本; (4)《兩當軒詩詞鈔》,道光年間“兩儀堂梓行”本。 以上各本與鄭補刻本、書帶草堂本構成一個序列,尋其源頭,皆可謂趙希璜《兩當軒詩鈔》增刻本之苗裔。其中《黃少尹集》為景仁侄兒錫申請江南河道總督、兩江總督麟慶捐資刊刻,書前有麟庆《黃少尹集序》,後有錫申《跋》。雖然黃錫申之名不見於民國《浮橋黃氏宗譜》卷一《世系圖》,[15]但為黃氏族人則毫無疑問。此是景仁親屬初次參與《兩當軒集》出版活動,對於後來咸豐、光緒年間黃志述夫婦三次刊刻《兩當軒集》不無先導意義。 (二)李澄編校《竹眠詞》四卷本與王昶鈔本 此一時期之《兩當軒集》新編本,既有詩集本,亦有詞集本,更有詩詞合刊本;而這些新編本往往與景仁遺稿及其傳鈔本,存在直接或間接關係。 第一種是道光八年()江都李澄(練江)編校《竹眠詞》四卷本。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李澄輯《夢花雜誌》五卷,後附《竹眠詞》四卷。書名頁題“竹眠詞”;正文署“武進黃景仁仲則著,江都李澄練江校”。卷首有王僧保、王昶兩序。僧保云: 黃仲則先生盛名滿天下,吾友李君練江謂其人激昂慷慨,不可一世,而落寞不得意。故其發于聲也,多不平之鳴。覽其豪情壯思,駸駸乎入稼軒之室。……《竹眠詞》板藏江都李君家,坊友戴燕孫請以行世,屬予校訂。……道光戊子(八年)冬儀徵後學王僧保敘。 從上可以推知,此本應為李澄編校,並刻書版。王僧保曾應戴燕孫之請,參與刊定。此四卷本《竹眠詞》按詞調(詞牌)編排,卷一有51個詞調(《虞美人》前後出現三次),共收92闋(目錄作“調”,下同);卷二有19個詞調,共收42闋;卷三有23個詞調,共收39闋;卷四有12個詞調,共收41闋。[16]合共個詞調,闋。 李澄編校《竹眠詞》四卷本 李澄編校《竹眠詞》四卷本,是第一部景仁詞集單刻本,且這種編排方式,不僅前所未見,也後無來者,故應予以高度重視。從王僧保《序》可知,李澄嗜好黃詞,因詞及人,有所契合,可謂仲則異代知音。應是出於玩賞之便,所以李澄將所得黃詞鈔本,按調重排,以便時加觀摩誦讀。以吳蔚光鈔本加以比對,可以發現此本兩個特點:一、吳鈔本按編年分為三卷,此本雖按調編排,但細察每調中各闋次第,則與吳鈔本大體一致。因此準確地說,此本是按調編年體。二、吳鈔本共錄黃詞作闋,此本亦闋,全見於吳鈔本。因此,儘管此本多有訛脫,然綜合以上兩點,充分證明其底本與據景仁遺稿過錄之吳鈔本有着同源關係。 至於此本之底本,可能來自王昶所藏景仁遺稿之傳鈔本。王昶曾差人往山西抄錄景仁遺稿,而此本所載王昶《序》云: 余聞仲則名久。乾隆戊戌,仲則來受業門下,始得盡見其詩。往往排蕩感激,如天風海濤,而隨手拈出,靡不入妙。又似麻姑狡獪,擲米都成丹砂也。顧常憙為詞,間出以示余。余謂詩與詞二,仲則既工詩,又欲於詞壇高寘一座,願不過奢耶?以詩為詞,不如不為矣。仲則笑而退。今讀其詞,固有可與詩並存者。惜仲則逝矣,徒增視予之痛耳。乾隆乙巳(五十年,)正月三日,述庵王昶。 序文撰於景仁卒後不到兩年,應是遺稿錄歸之時,王昶悲痛之情尤見諸筆墨之間。又,從序中可見王昶評價黃詞,在景仁生前、身後,顯得略有差異,但應沒有刊印之想,故此序當是王昶書於《竹眠詞》鈔本之題記。王昶編選《湖海詩傳》中黃詩後,“存全本於書塾中,以待後之篤嗜者之論定”,此一“全本”必然包括附有題記之黃詞鈔本。後來其被輾轉傳鈔,並落入李澄之手,遂有編校《竹眠詞》四卷本之舉。此本編排異於各種《兩當軒集》中之黃詞,且未為學界所關注。其中蘇州圖書館藏本,書名頁題“《兩當軒詞》,金粟山房藏板”,目錄和內文則作《竹眠詞》;卷首王昶《序》在前,王僧保《序》在後。其或為後印本,但上有批語,今據之收入《〈兩當軒集〉珍本選刊》。 (三)許玉彬等《兩當軒詩鈔》、《竹眠詞鈔》校刊本與吳蘭修校鈔本 第二種是道光十三至十四年(-)黎兆棠、許玉彬校刊本。此本書名頁題“黃氏仲則《兩當軒詩鈔》十四卷《竹眠詞鈔》二卷”,內題“道光十三年廣州重栞版本”。首吳尉光《原敘》,次景仁《自敘》,次趙希璜《校仲則詩付梓,不覺愴然》詩二首、鄭大謨《題兩當軒集》詩四首,次洪亮吉《行狀》、吳蘭修《小傳》。正文署“武進黃景仁著,順德黎兆棠校刊”。書後附鄭炳文《原跋》、許玉彬《後跋》。《後跋》云: 按是集所見凡三本,……(見上引)余與鍾君翼民、姚君掞藻喜讀是集,合諸本校而刻之。十四卷內《落花》二絕句已見九卷,作七律一首,題雖異而詩同,今刪去。從《湖海詩傳》補詩三首,從《悔存詩鈔》補詩一首,仍為十四卷。又得寫本《竹眠詞》一百三十六闋,寫本所無,從原刻《悔存詞鈔》補十四闋,從《詞綜》補三闋,仍為二卷,今稱《竹眠詞》者,從其多也。各本字句互有異同,茲依吳石華師所定,不復注云。道光十四年五月,番禺許玉彬跋。 可見此本《兩當軒詩鈔》是以趙希璜增刻本、鄭炳文補刻本等合校,又據《湖海詩傳》等增補而成。至於《竹眠詞鈔》二卷,則以“寫本《竹眠詞》一百三十六闋”為基礎,又據趙希璜本《悔存詞鈔》補14闋、《國朝詞綜》補三闋而成,共收黃詞闋。由此說明許玉彬等人旨在編出一部囊括他們當時能夠搜集到所有景仁詩詞之《兩當軒集》新本,即繼趙增刻本後第二個景仁詩詞合刊本。鑒於其在《兩當軒集》版本上之地位,今收入《〈兩當軒集〉珍本選刊》。 許玉彬等《竹眠詞鈔》校刊本 至於此本《竹眠詞鈔》所據“寫本《竹眠詞》”,即今澳門大學圖書館所藏《竹眠詞鈔》。書前有汪宗衍題記,云: 趙希璜刊本《兩當軒詩鈔》坿《悔存詞鈔》,僅七十九闋。道光間許玉彬重刊本改用吳蘭修校鈔本《竹眠詞鈔》,凡一百三十餘闋,詳見許跋。此鈔本標題、闋數、編次悉與許本同,書眉朱筆校記亦與許本合,當為吳氏手筆,即許刊之底本也。卷首有“桐華閣印”方印,吳氏著有《桐華閣詞鈔》,刊入《學海堂叢刻》中。甲申()小寒,宗衍記於椶蔭書屋。 此鈔本原為宗衍之父汪兆鏞所藏。兆鏞,學海堂專課生,師事陳澧,嗜好舊籍,藏書甚富。曾從陳澧四子宗穎處得吳蘭修《桐花閣詞》原刻本,發現《學海堂叢刻》本“刪汰過半”,遂於宣統三年()合編兩本重刻。吳蘭修(石華)任粵秀書院監課、學海堂山長,建樓“守經堂”於粵秀書院,藏書三萬餘卷。汪兆鏞與學海堂中人過從甚密,或許吳校鈔本原由學海堂舊藏,輾轉落入汪氏之手。此鈔本已收入《中國古籍珍本叢刊?澳門大學圖書館卷》,較便參閱。 關於吳蘭修校鈔本,黃志述《〈兩當軒集〉考異》卷上《諸家刻本目錄》“《兩當軒詩鈔》十四卷《竹眠詞》二卷(道光十三年番禺許玉彬等刻)”案語云:“詩依趙本校刊,李申耆師曰:‘詞為楊荔裳方伯選本’。”[17]其說有何依據,已難考知。但以楊芳燦《悔存詞選》與吳校鈔本比對,可以輕易發現兩者差異頗大,故此李申耆所言,似乎不很可靠。景仁一生遊跡未及嶺南,但友朋中卻有一些粵籍文人學士(如溫汝适、馮敏昌、潘有為、趙希璜、張錦芳),粵地也不乏黃詩喜好者(如黎簡、張維屏)。乾隆五十六年(),黃乙生隨調補新寧知縣萬應馨到廣東仁化,並攜景仁遺稿拜謁廣東巡撫朱珪。[18]因此《竹眠詞》流傳至嶺南,很可能始自乙生遊粵之時。此外,從吳蘭修校鈔本也可發現一些端倪。第一是題名。“竹眠詞”是景仁生前所命名,而“悔存詞鈔”之名則始自趙希璜《兩當軒詩鈔》增刻本。吳校鈔本與李澄編校本同名為“竹眠詞”,可見皆較接近景仁遺稿之題名。其次是編次。以吳蘭修鈔本與吳校鈔本比對,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即吳校鈔本第一闋至一百一十七闋與吳蘭修鈔本編次基本一致,可見吳校鈔本主體部分(前一百一十七闋)與黃氏家藏稿本關係密切,或即傳鈔自乙生遊粵時所攜景仁遺稿。[19] (四)吳修編《兩當軒詩集》十六卷本 以上所述各本《兩當軒集》,皆據景仁遺稿之傳鈔本進行編選刊刻;而吳修所編《兩當軒詩集》十六卷,則是第一部以遺稿為底本編刻之景仁詩集。此本書名頁題“《兩當軒集》,海昌蔣氏別下齋藏版”。首道光四年吳修《兩當軒詩集序》,次景仁《自敘》,次翁方綱《悔存齋詩鈔序》,次劉大觀《悔存齋詩鈔跋》,次吳蔚光《兩當軒詩鈔序》。次輯《兩當軒詩評》五則。次《兩當軒詩集總目》,題“海鹽吳修思亭編次”。正文為詩十六卷,間錄翁方綱、孫星衍等人評語。後附王昶《黃仲則墓誌銘》、洪亮吉《行狀》。最後為蔣光煦《跋》。後附《篝燈教讀圖題贈》四卷,乃蔣光煦為表彰其母馬氏所輯。吳修《序》云: 武進黃君仲則,詩名著乾隆間,没後名益重。……嘉慶初年,邱縣劉氏始刊《悔存齋詩鈔》五百首,長寧趙氏又刊《兩當軒詩鈔》八百餘首,顧前後多錯亂,且去取失宜,述庵少司寇嘗言之矣。君與同里孫觀察淵如、洪編修穉存、趙司馬味辛齊名,世稱孫、洪、黃、趙。三君者,余皆與遊處,相與上下其議論,獨未識君,而識君之子小仲,得讀君手定詩稾千一百篇,益歎服欣喜,欲為刊行,久而未果。今小仲亦歸道山,且無子,乃介丁君若士復假原稾,細為校閲,起癸未,終癸卯,凡二十年,年月先後,可按詩而得,遂編成十六卷,授之梓人,踐前諾以公同好。視趙氏所刻,多十之三。其間句字互異之處,指不勝數,魚豕之譌,悉為釐正。《行狀》稱篇幅完善者二千首,殆非手自刪存者耳。 此序撰於道光四年(),上距黃乙生去世已兩年。吳修(思亭)讀景仁詩,“思慕其人”,然因劉大觀本、趙希璜本未能反映黃詩全貌,遂從乙生處假得景仁稿本[20],時加奉讀,並欲刊刻。吳修曾將稿本交予丁履恆(若士),在乙生去世後取回;並按“年月先後”,始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終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編成第一部編年體景仁詩集。 吳修編《兩當軒詩集》十六卷本 道光七年(),此本開雕甫半,吳修先卒。蔣跋云: 海鹽吴君思亭,與先生之子小仲交,得其全槀,編成十六卷付梓,甫彫及半而吴君卒。今秋,其嗣君小亭將遠遊粤中,慨剞劂之未竟也,出以見贈。未一月而吴君家火,所藏籖軸皆為灰燼,獨斯集得免於厄,是若有呵護之者,豈文章有靈,不欲泯没於世邪! 跋文撰於道光十七年(丁酉,),蓋即此本完工之時,可見成書前後費十三年之久,歷經兩家之手,而其中曲折驚險處,讀蔣跋可想而知。今收入《〈兩當軒集〉珍本選刊》,以廣流傳。 四、兩種咸豐本及光緒本《兩當軒集》 咸豐八年,景仁孫志述先後刊刻《兩當軒集》二十卷本和二十二卷本,其中二十二卷本為所有《兩當軒集》中最全最好之本。而其後之光緒本等各種版本,皆源於兩種咸豐本。 (一)咸豐八年八月《兩當軒全集》二十卷本 早在道光末年,黃乙生“兼嗣子”黃志述[21]就曾多方搜集景仁遺稿,以及各種黃集刊本,詳加校讎,並擬梓行全集。志述於咸豐八年()正月才完成各本黃集《考異》。《〈兩當軒集考異〉序》云: 先大父詩集,始畢秋帆宮保選入《吳會英才集》,詞稿王蘭泉侍郎選入《詞綜》。厥後諸家稍廣之為專集,至吳思亭布經本,得詩千餘首而大備。惜其遽返道山,詞未付梓。道光戊申(二十八年,),吳君咨來歸詩詞原稿。蓋布經借錄後寄丁丈若士,輾轉相假,而吳君之尊人碩甫先生攜往秦、蜀、滇、黔,志述屢以書請,乃見歸也。志述既得原稿,因取諸家刻本參校之,得若干條,彙為《考異》二卷。原稿舊題《悔存鈔》及《悔餘存稿》,諸家以大父嘗取《史通?隱晦篇》“以兩當一”之語名軒,多題為《兩當軒集》,茲仍之。 可見直至道光八年,吳咨才應黃志述多次請求,歸還景仁稿本。志述根據稿本,撰集各本異同而成《考異》二卷,又彙編景仁全部詩、詞、文於一書,命名為《兩當軒集》。此外,志述在編校《兩當軒集》時,曾請毛慶善應允將其《黃仲則先生年譜》附入集中。故此毛慶善與季錫疇完成年譜初稿修訂後,將之寄予志述,並付刊刻。[22]季錫疇《〈黃仲則先生年譜〉跋》云: 《仲則先生年譜》,往於道光丁未歲與毛君叔美編纂,刻於尚友齋中。當時未得先生原稿,故僅據趙氏、吳氏刊本及洪氏《行狀》,與夫同人唱酬之作,參互鉤稽,仍不無缺略譌舛之憾。方欲重為搜輯,而毛君已歸道山,予迫羸老,未暇也。逮今歲戊午,仲孫得先生手定稿編纂付梓,乃得受而讀之,序次瞭然,十年遺憾,為之頓釋。因與陸君紫峰及仲孫重加刪訂開雕,惜乎毛君之不及見也。咸豐八年夏四月,太倉季錫疇識。[23] 從上可知,咸豐八年四月之時,景仁第一部“全集本”《兩當軒全集》已經基本編成。而今咸豐本中《黃仲則先生年譜》曾由季錫疇、陸黻恩(紫峰)據《兩當軒全集》進行過修訂,故與尚友齋本有所不同。 今見上海圖書館藏此本,書名頁題“《兩當軒全集》二十卷《考異》二卷《附錄》六卷”,內題“咸豐八年家塾校梓”。卷首景仁《自敘》,次吳儁所繪“仲則先生小象”及徐廷華題辭,次“《兩當軒集》校刊姓氏”,目錄後鐫“陽湖楊肇基、楊瀚雲合鐫”。卷一至十六為古近體詩,卷十七至十九為詩餘,卷二十為遺文(署“族子坤厚輯”)。後為《考異》二卷。附錄一為序跋,附錄二為傳狀志文,附錄三、四為唱酬題贈,附錄五為年譜,附錄六為詩話、先友爵里名字考。此本出於景仁稿本,既依循其編年體,且不僅詩詞合刊,又增加遺文一卷,所收景仁作品數量超越此前各本。同時,全書經黃志述校訂,在文本可靠性上亦超越此前各本。此外,《考異》二卷、《附錄》六卷,為研究景仁其人其作提供大量可貴資料。有鑒於此,學界對此本甚為重視,先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咸豐八年十二月《兩當軒集》二十二卷本 然而過往沒有注意到,在二十卷本《兩當軒全集》刊刻後,黃志述很快又進行補充,增刻成二十二卷本《兩當軒集》。[24]關於增刻過程,志述交代如下: 道光二十八年,志述得先大父手定詩槀十五卷、詞槀三卷,案時事皆止於乾隆辛丑()。續以吳思亭布經本所增詩二十七首,趙渭川員外所增詩三首,為今第十六卷,亦僅及壬寅()正月,下距易簀時尚年餘。且辛丑歲游太原、秦中,有詩二卷,見武虛谷知縣弔文,今其存者才數首爾。……後乃於書肆得壬辰至甲午(-)初稿一冊,去年十月校栞是集,謹摘其未刻者。而季丈菘耘、周君淳之、吳君敬叔各有錄示,並為補遺,分坿詩詞卷末。今年八月梓工告竣,莊君竹安忽於其家舊簏中撿得初槀百餘紙,蓋丙戌至壬辰(-)作也。吳刻所增者為辛丑夏日作,其手定槀亦在焉。大喜逾望,急取第十六卷校改之,而初槀蟲穿蠹蝕,塗注模糊,徐子楞、莊滌園、陸紫峰三先生及周君弢甫共為審定,去其重出者,得如干首,因裁并前刻補遺,都為二卷。於是《兩當軒集》統計有詩千一百七十首,詞二百十六闋。……壬寅以後詩詞,當即王蘭泉侍郎所稱《蔗梢集》。又《浮湘》、《渡淮》兩賦,《如無錄》二卷,皆見推於先輩,不知何時更得而備刻之也。咸豐八年冬十二月,孫志述謹識。 從上可知,二十卷本在咸豐八年八月刻成後,莊竹安忽於家中撿得景仁“丙戌至壬辰”詩作“初稿百餘紙”;志述遂取之校改第十六卷,又與徐廷華(子楞)、莊敏(滌園)、陸黻恩、周騰虎(弢甫)共同審定,去其重出,編成補遺二卷,二十二卷本《兩當軒集》在咸豐八年十二月刊成。 咸豐八年十二月本《兩當軒集》 今見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此本,書名頁題“《兩當軒集》二十二卷《考異》二卷《附錄》六卷”,內題“咸豐八年家塾校刊”。卷首景仁《自敘》,文次吳儁所繪“仲則先生小象”及徐廷華題辭,次“《兩當軒集》校刊姓氏”、“《兩當軒集補遺》校刊姓氏”。目錄後鐫“武進楊肇基、陽湖楊瀚雲合鐫”。卷一至十六為古近體詩,卷十七至十九為詩餘,卷二十為遺文,卷二十一、二十二為補遺,卷二十二後附黃志述《跋》。後為《考異》二卷,《附錄》六卷(同於二十卷本)。另補刻徐廷華詩一首、莊敏詩兩首、邵震亨詩一首,最後為季錫疇跋文。特別需要指出,卷二十一補遺收“古近體詩六十五首”,卷二十二補遺收“古近體詩五十五首、詩餘二首”,[25]全書共錄黃景仁“詩千一百七十首、詞二百十六闋”,故此本是各種黃集中最全之本。鑒於二十二卷本《兩當軒集》之重大價值,而且從未影印出版,學界知之甚少,今收入《〈兩當軒集〉珍本選刊》。 在兩種咸豐本《兩當軒集》刊印流傳後,分別出現據它們進行抄錄或翻印之本。二十卷本有同治十二年()集珍齋活字翻印本;二十二卷本有同治六年()劉履芬鈔本,此鈔本已收入《國家圖書館藏鈔稿本乾嘉名人別集叢刊》。 (三)光緒二年《重刊兩當軒全集》二十二卷本 咸豐本面世不及數載,太平天國軍席捲江南,咸豐十年()兵圍常州。光緒《武進陽湖縣誌》卷二十四《人物?忠節》載,黃志述“分守南門,城陷,巷戰死”[26]。而據謝蘭生《軍興本末紀略》卷三,黃志述卒於咸豐十年四月初六日。常州城破,咸豐本書版毀於戰火。志述妻吳氏“愴然念先澤之就湮,痛其夫畢生之志未能傳久”,遂“節縮衣食,勤力針黹”[27],積十數年所得,終於光緒二年()重刻《兩當軒集》。 此本書名頁題“《重刊兩當軒全集》二十二卷,光緒二年家塾校梓”。卷首黃景仁《自敘》,次“仲則先生小象”及徐廷華題辭,次汪昉《序》,序尾鐫“曾孫婿劉清泰蒓浦、曾孫男競執武校字”。次“《重刻兩當軒集》校刊姓氏”。正文二十二卷,後附《考異》二卷、《附錄》四卷。此本據咸豐二十二卷本翻刻,但刪去附錄中卷三、四“唱酬題贈”。清末以來,光緒本流傳較廣,成為坊間通行本,上海掃葉山房曾於宣統二年()據之出版石印本。 總之,同治以後各種《兩當軒集》皆源出咸豐本,然而翻印、傳鈔難免錯漏(如光緒本漏刻黃詩八首,集珍齋本錯誤亦在不少),故均不及咸豐二十二卷本之完善。 注釋 [1]包世臣:《齊民四術》卷六《黃徵君傳》,中華書局年版,第頁。 [2]洪亮吉《行狀》,黃景仁撰、翁方綱選編《悔存詩鈔》,清嘉慶元年()劉大觀刻本,第2頁。 [3]洪亮吉:《卷施閣文乙集》卷六《出關與畢侍郎牋》,《洪亮吉集》第1冊,中華書局年版,第至頁。 [4]轉引自許雋超、康銳編《黃仲則資料彙編》,黑龍江大學出版社年版,第頁;另參許雋超《黃仲則年譜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頁。 [5]翁方綱《序》,《悔存齋詩鈔》,第1頁。 [6]王昶:《湖海詩傳》,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影印清嘉慶八年()三泖漁莊本,第頁。 [7]景仁逝於山西解州安邑縣運城,蒲州臨近解州,王昶此處或為約略之詞。 [8]詳見許雋超《黃仲則年譜考略》,第頁。 [9]畢沅選輯:《吳會英才集》,清乾隆嘉慶間刻本。 [10]吉林大學圖書館所藏鄭炳文《兩當軒詩鈔》補刻本為民國王寯基故物,卷首有題記云:“鄭氏重刊跋謂‘取殘缺者補之,漫漶者修之’,蓋係就趙氏原刊補葺者也,故每頁字跡不同。其整潔無訛字、筆劃稍肥者,為趙氏原刊之板。”其說可資參考。 [11]詳參鄧駿捷《黃景仁詞集的流傳與版本考述》,《文學遺產》年第2期。 [12]袁通選編:《三家詞》,清道光十一年()袁祖惠刻本。 [13]王昶:《湖海詩傳》,第至頁。 [14]王昶、黃燮清、丁紹儀編:《清詞綜》第3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年影印本,第至頁。 [15]詳參許雋超《黃仲則年譜考略》,第至頁。 [16]此本目錄中卷四《洞庭春色》為“一調”,內文實為二闋;《賀新郎》為“十六調”,內文實為17闋,此處根據內文統計闋數。 [17]黃志述:《〈兩當軒集〉考異》卷上,《兩當軒集》二十二卷《考異》二卷《附錄》六卷,清咸豐八年()十二月黃氏家塾刻本,第1頁。 [18]詳參朱珪《知足齋詩集》卷十四《〈題黃仲則遺稿〉序》,見《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第頁。 [19]詳參鄧駿捷《黃景仁詞集的流傳與版本考述》,《文學遺產》年第2期。 [20]黃乙生所藏稿本是否即景仁運城遺稿,以及乙生如何得到此本,仍待查考。一種可能是,畢沅通過洪亮吉將遺稿交還乙生,以存先人手澤。 [21]《浮橋黃氏宗譜》卷六《譜圖指掌?四房》云:“志述,乙生兼嗣子,行一,字仲孫,一字廷颺。”詳參許雋超《黃仲則年譜考略》,第頁。 [22]毛慶善、季錫疇:《黃仲則先生年譜》,清道光二十七年()尚友齋刻本。 [23]毛慶善、季錫疇:《黃仲則先生年譜》,咸豐本《兩當軒集》附錄五,第14頁。 [24]詳參許雋超《黃仲則年譜考略》,第至頁。 [25]《兩當軒集》補遺所收兩闋黃詞,早已見於《兩當軒全集》卷十九之末,《兩當軒集》只是將其改刻於卷二十二。因此就黃詞言,二十二卷本實與二十卷無異。 [26]王其淦、吳康壽修,湯成烈等纂:《武進陽湖縣誌》,《中國地方誌集成·江蘇府縣誌輯》第37冊,江蘇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頁。 [27]詳參汪昉《序》,《重刊兩當軒全集》,清光緒二年()黃氏家塾本刻本,第1頁。 載《〈兩當軒集〉珍本選刊》卷首,許雋超、鄧駿捷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年10月版。 作者簡介 鄧駿捷,廣東南海人。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澳門文獻資訊學會會長,澳門近代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古代文學史料研究分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學研究,擔任《兩漢全書》、《清人著述總目》、《中國古籍珍本叢刊》的編委。主要著作有《劉向校書考論》、《明清文學與文獻考論》、《澳門古籍藏書》,古籍整理有《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校補)、《汪兆鏞文集》(合編)、《〈兩當軒集〉珍本選刊》(合編),書刊編纂有《澳門華文文學研究資料目錄初編》、《澳門文史論集》(主編)、《澳門文獻資訊學刊》(主編)等。 許雋超,年12月生,哈爾濱人。年6月,於南京師範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年8月起,為高校中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專任教師。現為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古籍整理與研究。已發表學術論文80餘篇,出版學術專書14部。 主編:呂亞南戴莉 學術支持:許雋超 歡迎關注:乾嘉同光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yiweia.com/dywry/7265.html
- 上一篇文章: 邹鲁探源之前人过年考
- 下一篇文章: 阳性丨这次是奶枣紧急寻人middot